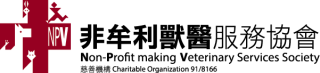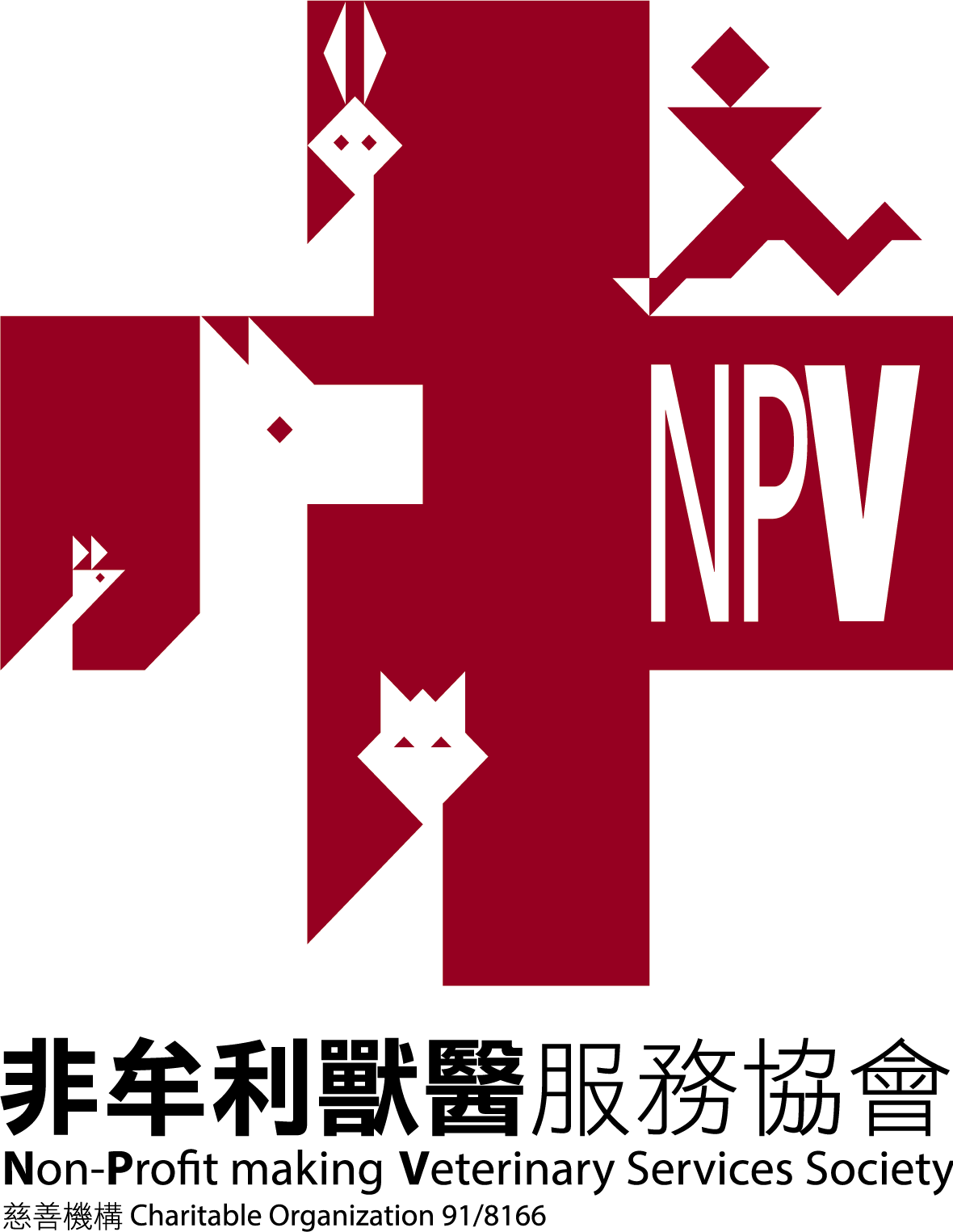八九六四 …維園的入口,良心的出口

談六四,可以有很多角度,可以牽動很多種不同的情緒。
六四對我來說基本上已是生命的一部份。年青時手電號碼是 xxxx xx64,足足花了接近十年時間才等到現在的xxxx 8964。 登記這個電話號碼的那一天激動得幾乎哭出來。 有朋友問我的電話號碼我會很驕傲的答:xxxx 天安門事件。當然以此來表示自己對六四的情意結是有點幼稚,但我的確很害怕終有一天會放下六四這個包袱,所以才堅持要等一個8964 的電話號碼來提醒自己:不敢忘記。
由當年在昔日的灣仔新華社聲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天真以為香港的力量不容小覷,到呼天搶地的示威遊行,到後來年年如是的悼念又悼念,二十三年來,當中的情緒早已被調節得理性而踏實。 六四,對我來說已不是一種社會運動,而是每年一次良心的退修會。
影響我很深的大學哲學啟蒙老師李天命教授,他教我們認識人生的兩種價值:工具價值和自身價值。或許六四燭光悼念晚會已失去了任何工具價值,再多人再多一百年的集會都不可能挽回當日在惶恐中殺那離開了靈魂,再多的燭光都不可能照亮黑壓壓的黑心,我們如大佛堅定不倒的意志也敵不過一兩個俗人對權力腐敗的慾望。平反六四?不可能是靠燭光晚會吧!
但燭光晚會還必定是要去的,因為它有它的自身價值。出席晚會就是代表一種態度, 這種「相信甚麼就一直堅持甚麼」的態度就是一種人生最高尚的情操與價值。 這種價值是普世的,與你是甚麼國藉甚麼政見甚麼黨派無關。
每一年就只有這一晚,我們可以放下分歧,由政客到高官到商家到富豪到中產到草根到露宿者,大家用可以用一個普通人的身份,共同憶想當日八九六四 的畫面:成千上萬的年青人,他們的思想還來不及說服自己的眼睛 — 不會吧,我的國家不會是真的要殺我吧 —- 坦克車已經輾過了他們的身軀。 難以署信的驚愕蓋過了身體的痛苦。 臨離去的一刻可能後悔了,可能內疚了,可能只想跟爸媽說一句對不起………..那怕是一下子的濫情,短暫釋放一下自己的良心,這晚過後,我們又可以回到自己的崗位,各自埋首血拼。
作為一個動物權益/福利工作者,我們每日都將「尊重生命」掛在口邊,可以找到一個理由開脫自己不去悼念六四嗎? 如果大家在「黃忍燭光悼念晚會」答應過我每年五月會出席動物的「六四」,悼念受虐殺的動物,那又如何可以鐵下心腸不去悼念那些同樣被「虐殺」的芳華正茂、揚眉威風的年青人? 在邏輯上不太講得通吧。
對於我來說,六四是一件大是大非的事,就正如月前反態膽藥業一樣。根本沒有討論的空間。 即是你沒有感動不去,也不可能有理由去反對別人去! 對那些長期拒絕或反對別人出席六四活動的人,他們是對大是大非失去了判斷力,還是不肯每年一次為自己的良心賣一次賬?
我很相信每年悼念六四的朋友,當中愛護動物的一定比不愛的多。因為愛護動物的朋友,都尊重生命,常存哀慟的心。
今晚, 親愛的朋友, 維園的入口,良心的出口,見。